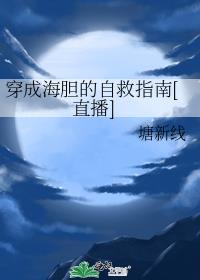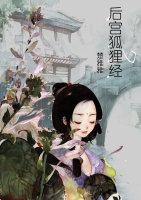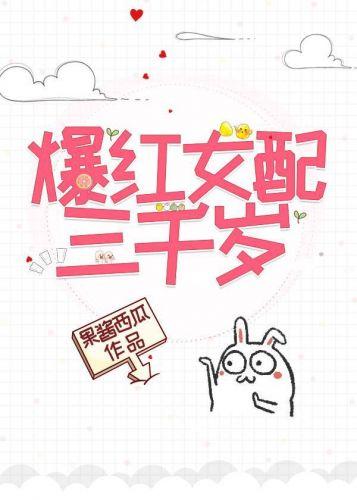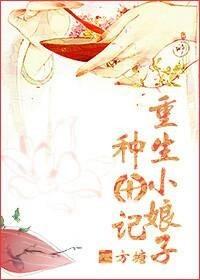器物文化
何先生說早上看熱鬧覺得那女孩形象很有特色,可一直沒有找到合适的時機。這裏不能拍照,但來都來了,不如參觀看看。如今的大廳撤了桌椅家具,供奉着先祖的雕像和祖輩們的牌位,擺上不少裝飾的壁畫木刻,供桌上面有不少的水果鮮花、糕點和酒,蠟燭點燃着,在煙中朦胧跳動着火光。這道門是額外收費參觀的,只有一兩個游客在裏面安靜的走走停停。供桌最上面是兩位先祖雕像,一左一右,聽說女老祖是古代的一個富家小姐,男老祖是入贅的,但不知道真假。最底下一排列的貢品,吃食占大多數,其次是鮮花,我不由得想到出生在困難年代的老一輩們,一陣感嘆,我們這代人現在活得很好了,每天都可以吃飽,生活很好,沒有戰争,沒有生命危險,可以一大家人在一起團聚,不用再害怕分離和颠簸了。桌子兩邊的柱子上貼着副對聯,“樹發千枝根共本 江水源同流萬派”,我想着如果那外國女孩是本家血緣,那可真的算得上是“發千枝”“流萬派”了。供桌附近有一張小方臺,上面擺滿了紅色布條,上面有些花紋,寫着平平安安,工作順利之類的吉祥話,比小臂要長。工作人員給我倆一人一條,說進這裏參觀可以拿這個紀念品,帶在身上是一種祝福和保佑。我把祈福布條放進包裏,何先生則直接系在了腰上。
我倆走進右邊,這裏東西亂的很,香爐的煙氣漫漫,牆上裝飾的紅色布帶一條條交錯着半挂在空中,燈籠掉了一個,幸虧裏面沒有明火,釘着的書畫也歪七扭八,霧氣袅繞中,一個人回頭撇了一眼,好像預見了有人要來。那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,染着淺黃色的頭發,修身的上衣沒過腿的長裙。她半個身體在暗光之中,臉上表情淡淡的,似笑非笑,有點滲人。我正要問怎麽回事,後面傳來工作人員的聲音,說着什麽幸好沒有去左邊展覽室,不然瓷器什麽的碎了就完了,說着兩三人走進來,告知有個野貓闖進來,現在沒找到,麻煩游客先離開,收拾好了再來參觀。那女人沒說什麽,擦着我的身邊出去了。
何先生沒有挪步子提議幫忙收拾,工作人員看是同事便感謝起來,我就跟着整理起來。這裏有很多書畫古籍,有做舊的痕跡,不知真假,我猜應該不是古董,真的古董放在這裏未免有點危險了。随手翻開一本,上面畫着八卦,星圖一類的東西,很粗糙的筆觸,是手寫的,圖的四周有着不少注釋,配合着泛黃做舊的紙頁,倒真的有點某個人筆記本的感覺了。注釋的字很淩亂,看起來都不像漢字了,有着不少删改增減,找不到觀看的順序,自然不明白表達的具體意思,便沒了興趣。轉頭看見何先生,他自然沒有幹正事,在翻看着什麽,我料到他提出幫忙絕對是有目的。我邊逛着邊扶正牆上的古畫,一幅幅的,畫了不少動物,有龍有狗有蛇的,我以為是十二生肖來着,直到看見了貓、鹿、狐貍,甚至有鱷魚,變色龍一類的動物,這一類動物在仿古的畫裏顯得不倫不類起來,顯得違和的很,不知道這是誰置辦裝飾的。走到何先生身邊,他在翻着一本圖冊,比一般書寬一點,裏面字少大多是圖,手繪的植物,各種花花綠綠的植物,畫的很細致,葉子花的特殊紋理都單獨放大畫着,看起來像是專業研究的記錄。何先生問我祖輩是否有從事相關的職業,比如藥理、醫學之類的,我搖頭解釋,這些書上的內容是祖輩留下來的,至于原本早成灰了,就算有長輩幹這行,也不知道是那一代人了。
忙了一陣子,右側展覽室收拾完畢,重新開放,我倆便轉身去了左側的房間。我想起了第一天遇到童謠,她就是從這裏竄出來的,進去一看,的确是舊舊的氛圍。這邊有不少的瓷器、鐵銅器皿、木雕等各式古物,這裏的東西不少都有點年頭,珍貴起來,被鎖在小玻璃罩裏讓人參觀。我駐足在一個梳妝盒邊,被鎖在玻璃裏,木頭盒子外面的雕刻很精妙,打開着裏面是一塊金絲邊紅方娟,上面有着一根金簪子,墜着玉白色的月牙片,很好看;梳妝盒內部有一面小圓鏡子,模糊着泛白,配合着旁邊的祥雲紋路,倒像是一輪滿月了。我繼續逛着,這邊有着個小銅鈴铛,挺大一個,裏面有鐵片,支架撐起來半懸着,推了一下,鐵片撞擊着發出清脆響聲,我猜這應該是古代的風鈴。風鈴這個東西我一直很喜歡,小時候別人喜歡布娃娃機器人,我不一樣,跑到精品店裏選了風鈴。那小東西主要是由玻璃海豚和金屬管組成的,海豚通體是水藍色,顏料上的不均勻,有的地方露出玻璃的本色,眼鏡就一個小黑點,點的大小不一,歪歪扭扭;金屬管有中指那麽長,深藍色的,有着金色的波浪紋路,質感很好,我經常摸導致後來漆都被蹭掉了。玻璃海豚和金屬管被幾條細線交錯串聯,中間夾雜着幾顆玻璃珠子,用手一碰,聲音很好聽,也許因為主體都是藍色,我小時候一直固執地認為這就是大海的聲音,這種認知一直到我後來真正看到大海才改變。這個風鈴遠看還可以,細看瑕疵不少,我卻一直寶貝着它,但時間跑起來,它的繩子斷了,小海豚也不知道躲哪去了,再後來我就長大了。